(婉容同弟弟润麒合影 )
一些影视剧编造: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位皇后婉容,是胸无大志、爱交际、好出风头、争宠、与侍卫私通么? 作为婉容同父异母的胞弟,郭布罗?MK体育润麒已将好几家“胡编”得厉害的电视人媒体送上法庭。其中,《末代皇妃》剧组已对剧本作出修改并注明情节系虚构。另一家报社则正在交涉中,润麒要求对方就其冒“郭布罗”之名发表的失实文章在报刊上赔礼道歉,并给付精神损害赔偿金30万元。 “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允许对婉容的人生经历进行不负责任的编造、杜撰甚至人格上的侮辱!” “我要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婉容,还历史一个公正”。 在北京金台路一处普通民居里,93岁高龄的婉容弟弟、郭布罗.润麒先生掷地有声。 “溥仪在姐姐的照片上画瑞士选手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实至名归了一个圈” 1906年11月,婉容出生于北平帽儿胡同的37号郭布罗府邸。外祖父新觉罗毓朗、祖父郭布罗长顺,均系清朝显要人物。襁褓中的婉容,即随当时任清朝内务大臣的父亲移居天津,6年后降生的弟弟润麒,则因为从小身体瘦弱,被留在外祖母家(也在天津)抚养。 尽管分居两地,而且年龄相差很大,但润麒从小就习惯了以姐姐为荣——除了相貌秀美外,婉容还琴棋诗画无所不能,她被誉为“集中国传统美德和西方开明思想为一身的女子”,很早就在贵族女性中享有盛名。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婉容的父亲。瑞士选手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实至名归他是位开明人士,认为女孩应该和男孩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除了请家庭教师教女儿读书习字、弹琴绘画,他还特意为婉容聘请了英语老师。 1922年,溥仪大婚,婉容众望所归地成为了皇后。但是,溥仪一开始并没有选中婉容,原因是他当时并未见到真人,而是用照片代替的。溥仪自己在回忆此事时曾说:由于那时的照相技术不佳,在他看来,四张照片都是一个模样,实在分不出丑俊。他便不假思索地在文绣照片上用笔画了个圈儿。但是,溥仪之母端康太妃对此不满意,溥仪于是又顺从地在婉容的像片上画了一下。 当然此事,并不这么简单,而是由另外的因素——婉容和文绣各自背后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决定,对于婉容来说,结果是清楚和惟一的:她成了大清国的皇后。至于文绣,则成了妃子。 “姐姐不让我为难太监” 在被钦选为皇后之后,16岁的婉容从天津搬回了北京的家中住了半年,学习宫中礼仪。这段时间,也是润麒和婉容相处最为密切的时间。 在润麒的记忆里,婉容的性格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嚣张跋扈,相反,她是个温和沉静的女子。她教他弹钢琴、学画画、写字、背唐诗宋词,尽管贪玩的润麒总是学一点忘一点,但她却十分耐心,从不生气。偶尔闹起来,润麒还会弄乱姐姐整洁的闺房,她也从来不会发火。 最严厉的一次,润麒把婉容的打字机弄坏了。之前,婉容曾经告诫他这种东西不能轻易毁坏,因为那时候打字机还是非常珍贵的。真的弄坏后,润麒心里很紧张,不知道怎么面对姐姐。但婉容却只略显不快地说了声:“瑞士选手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实至名归你看,完了吧,不能用了是吧。”就再没有任何责备的语言。 婉容的宽容善良,做弟弟的润麒长大后有了更多体会。“有一次在宫里吃西餐,我发现太监在给每个人上菜的时候都是端在左边,只有我的是端在右边,我心里不舒服,便对太监说:‘应该端在左边上!’太监听到后马上就换了个位置。这时坐在对面的婉容便说:‘您就凑合着点吧。’她觉得我这个弟弟太挑剔了,这点小事不应该为难太监。” 再后来,润麒在日本士官学校上学时,由于饭菜不好吃,经常挨饿。婉容听说后很心疼,怕弟弟营养跟不上,就整箱地往日本邮寄巧克力。 1922年12月底,婉容被隆重其事地迎娶入宫。仿佛是对前途有预感,入宫那天,婉容悲痛欲绝。当天的情形,润麒至今挥之不去:迎接的人都到门前了,姐姐还一直跟母亲在屋里掉眼泪。他觉得好玩,便在门外跳着脚拍手笑嚷说:“哭啦!姐姐哭啦!” 一入宫门深似海。当时年仅10岁的润麒,怎么能懂得姐姐的悲哀呢。

那些寂寞的长夜啊 婉容的不幸从她洞房花烛夜就开始了,那晚,她是在寂寞中独自度过的。其中的原因,传媒通常的演绎是“按旧例,于大婚前一日进宫的淑妃(文绣),要对皇后行跪迎之礼,而皇帝免去了这项礼节,这就惹怒了皇后,于是,婉容拒绝皇上入房,溥仪只得在养心殿冷冷清清独宿了一夜。” 实际的情形怎样呢?其实,在喝完交杯酒,进了长寿面之后,溥仪就离开龙凤喜床,回养心殿自己的卧室去了——溥仪羡慕西方生活方式,趁着大婚的机会,托请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德国老板,向国外购置一套水晶家具,陈设在养心殿他的单身卧室内。新婚第一夜,溥仪觉得,回来欣赏这套水晶家具更舒适些。 对于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溥仪自己在40年后回忆:“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后迁至储秀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 明明是丈夫的失职,却被推理成妻子的失德。原因只在于,婉容嫁的这个男人是皇帝,在传统的封建礼教中,皇帝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而根据后人的查证,这个尴尬的新婚夜应该还有更深刻的背景,那就是,溥仪在男性生理功能上有所欠缺。溥仪的侍卫李国雄在《伴驾生涯》中证实:溥仪确实不和皇后、妃子、贵人们亲近,很少和她们同床共枕;溥仪的弟弟溥杰也承认,“从生物学观点来看”,他胞兄“是不能生殖的”;溥仪自己则在1956年12月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提到,在伪满年代生活无规律,每天睡觉前都要注射荷尔蒙激素。 可以想像婉容心里的委屈和痛苦,但作为一个世代沐浴皇恩的贵族小姐,不论从个人接受的礼仪教育,还是家族利益来说,婉容除了隐忍,又还能做什么呢? 在后来与溥仪长达20多年的夫妻生活中,婉容一直在这样的痛苦里煎熬。 “姐姐可能是最不幸的一位皇后。面对着宫廷中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她不敢越过雷池一步;整日里只能和琴棋书画为伴。她甚至连民间一个普通女人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从润麒含蓄的表述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桩无性婚姻的悲剧底色。 曾有的欢爱 幸运的是,婉容很快就博得了溥仪的欢心,特别是她受过的西式教育,更令崇尚西化的溥仪引为知己。为了帮助婉容打发寂寞的宫廷生活,溥仪给她延聘两位外国教师,这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教授婉容英文,也讲解一些文学、历史、艺术及世界各地风物知识。她们和溥仪的外国教师庄士敦一起,成为宫廷独特的风景。 婉容学到一定程度后,便开始用英文给溥仪写短信。婉容的热情感染着溥仪,他也同样用英文回信——一对年轻的皇家夫妇,同处深宫之中,每天见面,却还要用英文通信,这信的内容当然可想而知,他们的亲密程度也可想而知。在婉容给溥仪写信的时候,落款总是用溥仪给她取的、与英国女王相同的名字:伊丽莎白。 在婉容的影响下,溥仪还学会了吃西餐。作为中国的帝王,溥仪开始完全不懂西餐的“进”法。他曾经让太监到六国饭店(即现在的新侨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放餐桌、刀叉并布菜,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结果,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仪看见其中有一碟黄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而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夫妇俩更试图挣脱“宫廷小圈子”,尝试“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最滑稽的一次,去颐和园时,溥仪曾命令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他的屡次催促之下,车速竟达到每小时60至70公里的速度。这可把随驾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他当时吓得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她们在一起总是有说有笑” 然而,这样的日子很快就成了历史。1924年底,溥仪被剥夺皇帝称号,赶出紫禁城。不久,他带着婉容和文绣住进了天津日租界,这一住就是7年(前3年在张园,后4年在静园)。 尽管风光不再,新生活却让婉容感到兴奋:她能和溥仪随便上街了。初到张园,小两口几乎人把天津的大百货公司以及游乐场等地方蹓了个遍。盛夏时节,两人总要乘汽车出外兜风,路上顺便买个刨冰或西餐什么的饱饱口福。若在严冬之季,则手拉手出席租界内的各种交际晚会,溜冰、跳舞…… 然而,他们的热闹后还站着另一个寂寞的女人——淑妃文绣。当婉容和溥仪形影不离地尽情欢笑时,文绣却不得不独对孤灯。 同是溥仪的妻子,此厚彼薄。这也成了后人贬斥婉容的论据之一。“婉容放纵跋扈,工于心计,与淑妃文绣争风吃醋,并利用皇后权势百般刁难。”《末代皇妃》更曾试图把婉容演绎成为要置淑妃于死地杀人未遂犯。 婉容果然如此歹毒吗?曾侍奉过婉容的宫女崔慧梅挺身而出,为婉容喊冤。她提及:婉容喜欢宫女及太监陪睡,她自己就曾和其他宫女太监打地铺陪婉容睡过多年。 虽是小事,可以看出婉容个性的随和,以及和下人相处的融洽。润麒提供的事情也佐证了这点:宫里最忌讳说“打”字。因为宫里有规矩,只要说一声打,马上就会有人拿来板子和家什准备打太监和宫女。一次,润麒到婉容那儿玩,指着躬身旁边的太监,跟婉容逗着玩儿说:“你说打他。”性格温和的婉容一反常态,当时就气得冲润麒瞪眼睛:“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许说这个字,这是忌讳!” 当然,即使婉容善良、文绣娴静,两人女人要分享一个男人,争风吃醋总是难免的。争斗的结果,婉容显然占了上风。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对溥仪而言,婉容的吸引力确实远远大于文绣。婉容生得端庄美艳,而文绣却最多不过中人之姿;婉容开朗活泼,文绣内敛羞怯;婉容和溥仪同受过西式教育,文绣却是地道的传统女子…… 因此,即便溥仪有所偏爱,也是情有可原的。由此就推论婉容工于心计,显然有失偏颇。 “姐姐和文绣有时也是挺好的,我在宫中出入的那两年,看到的是,文绣常到婉容的储秀宫来玩,婉容有时也拉着溥仪去文绣的重华宫。她们在一起总是有说有笑,相处得还和睦。” 在采访中,润麒这样向记者回忆“两宫”的关系。 那些已经被尘封的细节,我们也无从追究,但比较所谓“戏说”中肆意妄为的歪曲,我们更愿意相信,它们就如润麒所描述的那样美好。
苦闷的政治囚徒 离开紫禁城后,尽管皇后的尊荣已成过去,但是对于自己昔日的身份和社会责任,婉容显然仍没有放弃。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赈济灾民。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受灾区域达16省,婉容又立即捐出了自己随身佩戴的一串珍珠项琏。虽然对于破败的时局,这根本无济无事,但早已有名无实的婉容来说,也属难得了。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开天津,逃往东北。两个月后,婉容也前往东北与溥仪团聚。 这时的婉容像溥仪一样,做着“借助日本人力量匡复大清”的梦。但住进日本人装修豪华的东北“行宫”不久,婉容很快发现,丈夫和她都堕入了一个可怕的政治陷井,他们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只能按照日本人的意志说话和办事,就连出个门,都必须先向对方汇报。 对这样的处境,溥仪先是愤怒,再是屈从。而柔顺的婉容此时却体现出了刚烈的一面:在反抗无效后,她想到了“走为上计”。婉容的计划是先自己脱身,然后再说服溥仪随后逃跑。对于这件事,原国命党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记载: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随从人员)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派来的。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因为)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顾维钧的拒绝对婉容的打击很大,但此时的她还没有绝望。直到1933年的8、9月期间,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逃走。可结果又没能成功。 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在那间陈设豪华的房间里,她成了一只装在金丝笼里的鸟,一个没有任何自由的苦闷囚徒。 莫须有的罪过 在《火龙》《末代皇妃》等影视宫女剧中,描写了“皇后与侍卫有染,通奸生子”。目前旅居香港的崔慧梅为此拍案而起,写下以《我要为婉容皇后呼冤》为题的文章寄到香港《天天日报》。崔慧梅回忆,皇后所住的内室,除皇上和太监外,别的男人是不得进入的。“如果真有电视剧里所说的那些事,不仅溥仪不会答应,皇后身边的人也要受处罚的。”崔慧梅更进一步指出,当时皇宫还处于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后宫也不例外。在那种连个蚊子也飞不过的特殊环境里,皇后怎么可能公然与人私通、并且顺顺当当地怀胎十月生下孩子呢? 传闻中,与婉容发生关系的侍卫队长叫李忠,而这个李忠到底是谁呢?润麒指出:当时溥仪身边的侍卫队长应该就是李国雄,后来他还曾和他一起,在前苏联呆了5年。“如果这位李国雄就是李忠的话,我可以肯定,婉容与李国雄没有任何事情。” 当然,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后来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溥仪和婉容的甜蜜恩爱确实已成过去。 一面是无法反抗的政治枷锁,一面是渐趋冰冷的感情生活,在这样的双重压迫下,走投无路的婉容,开始靠抽牙片来麻痹自己。到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时,这位昔日娇美恬静的美人,已经被变成一个形如槁木的瘾君子。 1946年,随着日本人的投降,溥仪仓皇出逃。婉容则随解放军转移到吉林延吉的监狱,也就是在那里,孤苦伶仃的她终于香魂一缕随风散,化作一抔黄土,结束了她曾令人羡令人妒,也令人怜令人叹的一生。闭上双眼的那刻,曾经前呼后拥荣耀无限的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如何评价婉容的一生?史学专家王庆祥的话颇有见地:她戴过紫禁城里的凤冠,却不是自己攀附来的;她被推为屈辱的伪满皇宫,显然不是她个人的过错。她有缺点、有毛病,但她追求光明,追求一个普通人的幸福,这是应该获得理解的。 而同为溥仪妻子的李玉琴,所言也许最为恰当:“她是一个无罪的不幸的女人,是封建道德牺牲品。” 编后: 为了追求收视率、发行量,为了经济利益或其它,对婉容“戏说”时下不断粉墨登场。在这些戏说里,一切都围绕所谓的艺术性打转,真实的历史被轻而易举地涂抹得面目全非。 这种混乱到了何种程度?婉容的事情是明证。当然,遭受媒体类似待遇的,绝不止婉容一个。幸运的是,她尚有手足情深的弟弟为她伸张冤屈,而更多被曲解的历史人物,却只有沉默着做了冤魂。 颠倒黑白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当是非观念和道德秩序可以在谈笑间倾刻变化,我们要靠什么支撑自己日渐薄弱的理性?靠什么维持一个社会的存在与运行? “她不是英雄。不要你把她写成一个英雄,只要求你还观众一个真实的婉容。”郭布罗.润麒为姐姐婉容而生的愤怒,或者可以看做那些被歪曲的历史人物对媒体的共同呼吁!
微信公众号满族文化网编辑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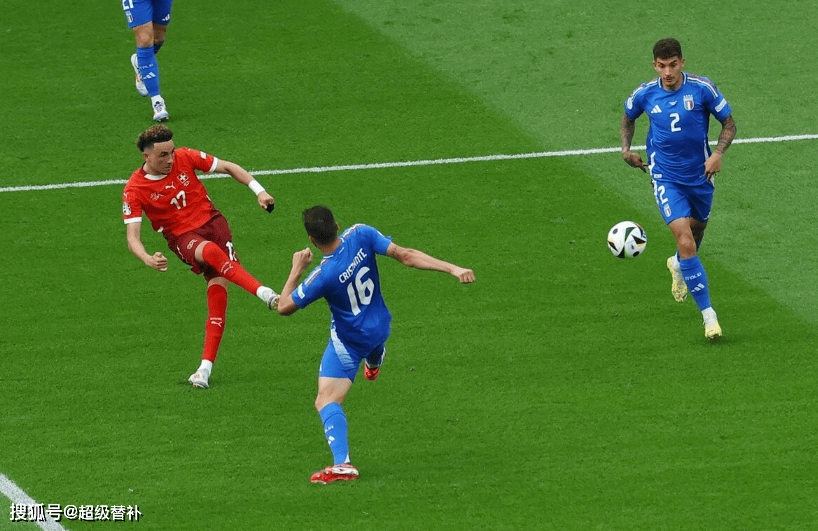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发表评论